[转帖]论德意志气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6:50:44
<P>意志气质:决定论的进程
在表面上看来,德意志气质中充满了矛盾。这些矛盾中的一些似乎是尖锐和根本性的。但是通过深入的考察不难获致这样一个结论:德意志气质所表现出的矛盾经常是源自观察者的误解和成见。事实上德意志气质不仅具有逻辑清晰的一致性,而且具有内在的稳定性。或许,正是后者使前者可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得以保持。
 </P>
</P>
<P>德意志气质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理想主义的精神勇气(不幸,这是有争议的。但是作者希望这种出于误解的争议在随后的文字中将得以澄清)。今天的德意志气质所包含的主要精神内涵可以追溯到前基督教时代的古日尔曼神话。主神奥丁和他的勇士们在与魔界的战斗中同归于尽,世界也随之毁灭。这类悲剧性的结尾从希腊时代就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是日尔曼的悲剧更狂暴、刚健,具有一种可怕的冷静和客观。正义者没有获得任何安慰性的奖赏,即使仅仅是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奖赏。没有牺牲的光荣,也没有受难的神圣。甚至正义本身也随着她的承载者一起寂灭。客观而言,这个世界确实既无价值也无意义。“在日耳曼神话中,战争就是自然界的秩序,就是生命的基本要素”(《德意志人》,埃利希-卡勒尔著,商务印书馆)。
这种植根于久远历史中的刚健的集体无意识和发自天性的英雄主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成为德意志斯多葛主义世界观和精神气质的心理基础。并在尼采的哲学和瓦格纳的戏剧中获得了众所周知的诗意化的复兴和发扬。一位在一战中阵亡的普通德国士兵在他的家书中典型地总结了这一点:“德国人向来把死亡看做高尚人生的完成。。。”(《向死而生》,德国文化丛书,三联出版社)。这里,死亡不再是一种纯粹否定性的东西,而被赋予某种终极的积极意义。
如果说哲学和艺术由于具有一定程度的精英特征而可能缺乏最广泛的平民意义和统计一般性的话,那么通过考察作为一种大众化宣传手段的军歌可以有效弥补精英特征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为宣传必须面向大众,符合大众的心理状态和需要。以纳粹德国时期著名的《德国装甲兵之歌》和《德国伞兵之歌为例》:
德国装甲兵之歌
“。。。。。。
跃上那冲向胜利的通途!
如果我们为命运女神所抛弃,
如果我们从此不能回到故乡,
如果子弹结束了我们的生命,
如果我们在劫难逃,
那至少我们忠实的坦克,
会给我们一个金属的坟墓。”
(歌词译文)
“。。。。。
Und kehren wir nicht mehr,
Zur Heimat zurck,
Trifft uns die Todeskugel,
Ruft uns das Schicksal ab,
Ja Schicksal ab,
Dann ist unser Panzer
Ein ehernes Grab。”
(德文歌词)
 </P>
</P>
<P>德军战斗油画
德国伞兵之歌
“。。。。。。
同志们,那是有去无回的征途。
在遥远的东方有黑色的云彩,
来,不要失魂落魄,来!”
(歌词译文)
“。。。。。。
Kamerad, da gibt es kein zurueck。
Fern im Osten stehen dunkle Wolken,
Komm' mit und zage nicht, komm' mit!”
(德文歌词。歌词共三段,每一段均出现了“同志们,那是有去无回的征途。”)
 </P>
</P>
<P>德军战斗油画
在这两首以激励士气和纪律精神为目的军歌中,死亡(而并非失败,这个差别是意味深长的)被毫不隐讳地提及。这种不同寻常处理的源于建立在清醒的现实感之上的勇气,也源于对自我、死亡和责任的深刻而独特的理解所带来的精神力量,在一般意义上反映了古北欧神话所代表的独特死亡观念对于现代德意志民族的大众心理特征的深远影响。
纪律和服从是德意志民族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这里引人注目的原因不仅在于其自身的彰显性,还源自与德意志式勇气之间的“对立”。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兴亡》中表达了这样的诘责:“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在战场上视死如归。。。却在尘世的权威面前唯唯诺诺。。。”。类似的疑问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不同的思考者也就此给出过不同的答案。事实上,循着德意志斯多葛主义的精神源头,勇气和服从之间表面上的矛盾可以被自然和清晰地理解。
古日尔曼人始终被罗马文明所吸引着,即使最严酷的汪达尔日尔曼人也对罗马文明怀有深厚的敬意。但是本能中对自由的渴望和斯多葛气质却使得他们的灵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被罗马所代表的文明生活方式同化。战斗的天性使得日尔曼诸族成为罗马的保卫者,又不可避免地成为罗马的破坏者和征服者。罗马时期的保卫和破坏,服从和抗争,如同一个隐喻,暗示了德意志民族在其后颇为漫长的历史中的命运。
法兰克王国分裂后,由于天性中对自由的追求和或许过度的战斗精神,德意志人路易的领地上未能象西法兰克那样长时间地维持着一个基础稳固的统一民族国家。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来自日尔曼法兰克王室的秃头查理在高卢凯尔特人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权威,而这种权威的绝对性是大多数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德意志的土地上从未获得过的。神圣罗马帝国由于组织松散、内部的征战和罗马教廷势力的渗透而变得如此弱小,以致她经常无法象同时期的法国、西班牙甚至丹麦那样赢得大陆国家的尊敬。这使得德意志成为强大和弱小矛盾体。
幸运的是,曾经使得德意志人无法融入罗马文明的斯多葛气质最终将帮助德意志摆脱涣散和内部争斗的宿命。日尔曼诸部落毁灭罗马之后,某种不安和负疚感时时支配着作为胜利者的日尔曼诸王的情绪。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不安源于对秩序和圣化的价值体系的渴望,反映了德意志气质中一种深刻而独特的方面:强大的争取自由的倾向,与一种同样强大的为某种奉为神圣的秩序和权威而献身的冲动相互交织的精神需求。只有从斯多葛主义的视角中,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才可能真正得以消解:自我主义者的行为模式是一致而容易理解的,他们追求个人自由,在享受自由所带来的任何乐趣的时候也不会有患得患失的负疚感;但斯多葛主义忽视自我、追求使命和责任的本质诉求使得斯多葛主义者的个人幸福的的终极实现无法简单地通过自我需要的满足来达致,而必须借助于某种外在秩序和价值体系的认同。
 </P>
</P>
<P>条顿骑士
这种斯多葛气质在德意志漫长的历史中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逐渐得到了社会化或学院化的发展。如黑暗时代的亲兵制度、行会、条顿骑士团、晚近一些的普鲁士军官团,以及德意志古典理想主义。条顿骑士三誓言:“安贫,守贞,服从”和伊曼纽尔-康德的著名命题:“理应即能够”(Ought implies can,英译) 典型地反映了德意志斯多葛主义对于黑暗时代和古典时代德意志人的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影响。
使得德意志斯多葛主义在德语民族的精神世界中发生最广泛和深刻的作用,并根深蒂固地成为近、现代德意志人精神气质的基本要素的代表性事件或许应该归结为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和宗教改革领袖路德对德意志斯多葛主义的继承、发展和独特诠释。路德的宗教改革,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德意志民族完成了获致精神平衡与内心宁静的自我精神建构;另一方面,为德意志摆脱政治上的涣散和重新崛起奠定了心理-文化的基础,并争取了必要的政治环境。
路德首先是一个典型的德意志人。“在路德身上,抗争的冲动和服从的冲动同样强烈。。。一方面,他那叛逆的天性和对自由的渴望,使得他提倡在精神上只服从上帝,这种服从,就是在个人领域内的绝对自由,因为不从属任何种类的人的控制和监督。另一方面,他对秩序和价值的需求以及征服本人和其他人身上邪恶力量的愿望,又使得他主张在政治领域中服从世俗权威”(《德意志人》,埃利希-卡勒尔著,商务印书馆)。出于这种考虑,路德创造性区分了精神自由和肉身自由,主张人应该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应该尽己所能在精神接近上帝的终极存在;同时,要求在世俗生活中,必须克制个人欲望和物质需求,通过服从和克己来摆脱生物本能力量对于自我的支配和控制,获致最大限度的精神自由。
在其他文化中,克己和苦行的观念虽然也时常被提及,但是通常难以成为主流和常态,或者需要借助类似于后世和因果报应这样的观念来帮助信仰者保持精神和情绪的平衡。例如,虽然中国理学中有“灭人欲,存天理”之说,但是中国的自由观中居主导地位的始终是“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式的天人合一,即精神-肉体相统一的自由观;而佛教的现世苦修思想与因果报应和轮回之间有着很难否认的心理关联。与此不同的是,德意志的自由观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洽的:通过区分精神自由和肉身自由,赋予精神自由某种终极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将精神上的自由和行动上的严谨守纪言之成理地统一起来。这种诠释的深层心理动因构成了德意志气质中独特和深刻的一面,也是“德意志力量”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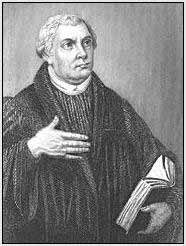 </P>
</P>
<P>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
<B>德意志气质:历史的光影</B>
写这一节时,恰逢7月20日。也许,58年前那段历史的几羽碎片,是这篇小文最好的总结。
Stauffenberg上校重伤之后,本可退役,就此离开战争和危险。可是责任感使他做出了相反的选择:“虽然我残废了,可是我还有一个神圣的使命要去完成。。。总参谋部的每一名军官都有责任行动起来,挽救德国”。他对病榻前的妻子如是说。7-20行动失败后,Stauffenberg未经审讯,即被忠于希特勒的军队枪决。
同样是出于责任感,Rommel沉思之后承诺:“我有责任做些事情来挽救德国。。。告诉他们,可以指望我”。说这番话时,Rommel已经达到了作为一个军人所能达到的荣誉颠峰,即使在敌人那里,他也受到了普遍的尊重。无论战争以何种方式结束,即使战败,也并不妨碍他继续自己体面的军人生涯和宁静的家庭生活。对Rommel个人来说,投身贝克的密谋集团是一场不公平的赌博,他几乎不可能再为自己赢得什么,却可能失去一切。但是,由某种可贵的品质所驱使,他做出一个最终为之牺牲生命的选择。
事实上,密谋者们在最后一次行动之前,并不缺乏必要的现实感,已不再对“体面的和平”抱任何幻想。他们清楚,自己的行为可能仅仅是一种象征、一个符号。但他们显然认为,人是值得为了正当的精神牺牲生命的:
“要不惜一切代价行动起来。即使不能成功,也必须尝试在柏林夺取权力。事情的关键已经不再是政变的实际目的,而是向世界和历史证明德国的抵抗者勇于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和这个目标相比,其他的事情已经不再重要。
“我们之中的人没有理由抱怨死亡,因为任何加入这个行列的人已经穿上了内萨斯的衬衫。只有当一个人愿意为信仰而牺牲时,他才得以建立自己的道义价值”。
以上言语出自Henning von Tresckow将军。长期在东线服役的Tresckow是密谋的主要发起人和策划者之一。不同寻常的是,严酷的生存之战并未使他成为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这种将实际事务中的精明干练和深沉的理想主义精神气质结合在一起的能力,是日耳曼民族的一个独特之处。事败后,Tresckow独自来到无人的阵地,用一颗手榴弹炸掉了自己的脑袋。
7-20事件的抵抗者们用自己的行动例示了德意志气质中最可贵和显著的特征:勇气、理想主义的精神力量和建立于清醒的现实感之上的自我牺牲。这些品质与由虚妄的宗教狂热所诱发的 “勇敢行为”有本质的区别。如同道德价值必须建立在人的自由意志和自主选择之上,勇气价值也必须建立在清醒的现实感之上。毕竟,在高楼屋檐上行走的孩子不是因为真正的勇敢,而是出于无知和虚妄。
在中国人眼里,密谋者最后的牺牲或许有些过于理想主义了。但是这种指责必然是出于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抵抗者在7-20事件中的牺牲精神和道德勇气始终在帮助战后的德意志民族重建自己的精神世界。这对德国人是尤为重要的,他们需要一种言之成理的形而上学和严肃的精神生活。
 </P>
</P>
<P>“如果不把生命看做是为神圣使命而必须履行的责任,一个人才可能怕死”
Claus Graf Stauffenberg(1907-1944)
</P><P>意志气质:决定论的进程
在表面上看来,德意志气质中充满了矛盾。这些矛盾中的一些似乎是尖锐和根本性的。但是通过深入的考察不难获致这样一个结论:德意志气质所表现出的矛盾经常是源自观察者的误解和成见。事实上德意志气质不仅具有逻辑清晰的一致性,而且具有内在的稳定性。或许,正是后者使前者可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得以保持。
 </P>
</P>
<P>德意志气质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理想主义的精神勇气(不幸,这是有争议的。但是作者希望这种出于误解的争议在随后的文字中将得以澄清)。今天的德意志气质所包含的主要精神内涵可以追溯到前基督教时代的古日尔曼神话。主神奥丁和他的勇士们在与魔界的战斗中同归于尽,世界也随之毁灭。这类悲剧性的结尾从希腊时代就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是日尔曼的悲剧更狂暴、刚健,具有一种可怕的冷静和客观。正义者没有获得任何安慰性的奖赏,即使仅仅是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奖赏。没有牺牲的光荣,也没有受难的神圣。甚至正义本身也随着她的承载者一起寂灭。客观而言,这个世界确实既无价值也无意义。“在日耳曼神话中,战争就是自然界的秩序,就是生命的基本要素”(《德意志人》,埃利希-卡勒尔著,商务印书馆)。
这种植根于久远历史中的刚健的集体无意识和发自天性的英雄主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成为德意志斯多葛主义世界观和精神气质的心理基础。并在尼采的哲学和瓦格纳的戏剧中获得了众所周知的诗意化的复兴和发扬。一位在一战中阵亡的普通德国士兵在他的家书中典型地总结了这一点:“德国人向来把死亡看做高尚人生的完成。。。”(《向死而生》,德国文化丛书,三联出版社)。这里,死亡不再是一种纯粹否定性的东西,而被赋予某种终极的积极意义。
如果说哲学和艺术由于具有一定程度的精英特征而可能缺乏最广泛的平民意义和统计一般性的话,那么通过考察作为一种大众化宣传手段的军歌可以有效弥补精英特征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为宣传必须面向大众,符合大众的心理状态和需要。以纳粹德国时期著名的《德国装甲兵之歌》和《德国伞兵之歌为例》:
德国装甲兵之歌
“。。。。。。
跃上那冲向胜利的通途!
如果我们为命运女神所抛弃,
如果我们从此不能回到故乡,
如果子弹结束了我们的生命,
如果我们在劫难逃,
那至少我们忠实的坦克,
会给我们一个金属的坟墓。”
(歌词译文)
“。。。。。
Und kehren wir nicht mehr,
Zur Heimat zurck,
Trifft uns die Todeskugel,
Ruft uns das Schicksal ab,
Ja Schicksal ab,
Dann ist unser Panzer
Ein ehernes Grab。”
(德文歌词)
 </P>
</P>
<P>德军战斗油画
德国伞兵之歌
“。。。。。。
同志们,那是有去无回的征途。
在遥远的东方有黑色的云彩,
来,不要失魂落魄,来!”
(歌词译文)
“。。。。。。
Kamerad, da gibt es kein zurueck。
Fern im Osten stehen dunkle Wolken,
Komm' mit und zage nicht, komm' mit!”
(德文歌词。歌词共三段,每一段均出现了“同志们,那是有去无回的征途。”)
 </P>
</P>
<P>德军战斗油画
在这两首以激励士气和纪律精神为目的军歌中,死亡(而并非失败,这个差别是意味深长的)被毫不隐讳地提及。这种不同寻常处理的源于建立在清醒的现实感之上的勇气,也源于对自我、死亡和责任的深刻而独特的理解所带来的精神力量,在一般意义上反映了古北欧神话所代表的独特死亡观念对于现代德意志民族的大众心理特征的深远影响。
纪律和服从是德意志民族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这里引人注目的原因不仅在于其自身的彰显性,还源自与德意志式勇气之间的“对立”。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兴亡》中表达了这样的诘责:“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在战场上视死如归。。。却在尘世的权威面前唯唯诺诺。。。”。类似的疑问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不同的思考者也就此给出过不同的答案。事实上,循着德意志斯多葛主义的精神源头,勇气和服从之间表面上的矛盾可以被自然和清晰地理解。
古日尔曼人始终被罗马文明所吸引着,即使最严酷的汪达尔日尔曼人也对罗马文明怀有深厚的敬意。但是本能中对自由的渴望和斯多葛气质却使得他们的灵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被罗马所代表的文明生活方式同化。战斗的天性使得日尔曼诸族成为罗马的保卫者,又不可避免地成为罗马的破坏者和征服者。罗马时期的保卫和破坏,服从和抗争,如同一个隐喻,暗示了德意志民族在其后颇为漫长的历史中的命运。
法兰克王国分裂后,由于天性中对自由的追求和或许过度的战斗精神,德意志人路易的领地上未能象西法兰克那样长时间地维持着一个基础稳固的统一民族国家。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来自日尔曼法兰克王室的秃头查理在高卢凯尔特人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权威,而这种权威的绝对性是大多数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德意志的土地上从未获得过的。神圣罗马帝国由于组织松散、内部的征战和罗马教廷势力的渗透而变得如此弱小,以致她经常无法象同时期的法国、西班牙甚至丹麦那样赢得大陆国家的尊敬。这使得德意志成为强大和弱小矛盾体。
幸运的是,曾经使得德意志人无法融入罗马文明的斯多葛气质最终将帮助德意志摆脱涣散和内部争斗的宿命。日尔曼诸部落毁灭罗马之后,某种不安和负疚感时时支配着作为胜利者的日尔曼诸王的情绪。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不安源于对秩序和圣化的价值体系的渴望,反映了德意志气质中一种深刻而独特的方面:强大的争取自由的倾向,与一种同样强大的为某种奉为神圣的秩序和权威而献身的冲动相互交织的精神需求。只有从斯多葛主义的视角中,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才可能真正得以消解:自我主义者的行为模式是一致而容易理解的,他们追求个人自由,在享受自由所带来的任何乐趣的时候也不会有患得患失的负疚感;但斯多葛主义忽视自我、追求使命和责任的本质诉求使得斯多葛主义者的个人幸福的的终极实现无法简单地通过自我需要的满足来达致,而必须借助于某种外在秩序和价值体系的认同。
 </P>
</P>
<P>条顿骑士
这种斯多葛气质在德意志漫长的历史中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逐渐得到了社会化或学院化的发展。如黑暗时代的亲兵制度、行会、条顿骑士团、晚近一些的普鲁士军官团,以及德意志古典理想主义。条顿骑士三誓言:“安贫,守贞,服从”和伊曼纽尔-康德的著名命题:“理应即能够”(Ought implies can,英译) 典型地反映了德意志斯多葛主义对于黑暗时代和古典时代德意志人的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影响。
使得德意志斯多葛主义在德语民族的精神世界中发生最广泛和深刻的作用,并根深蒂固地成为近、现代德意志人精神气质的基本要素的代表性事件或许应该归结为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和宗教改革领袖路德对德意志斯多葛主义的继承、发展和独特诠释。路德的宗教改革,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德意志民族完成了获致精神平衡与内心宁静的自我精神建构;另一方面,为德意志摆脱政治上的涣散和重新崛起奠定了心理-文化的基础,并争取了必要的政治环境。
路德首先是一个典型的德意志人。“在路德身上,抗争的冲动和服从的冲动同样强烈。。。一方面,他那叛逆的天性和对自由的渴望,使得他提倡在精神上只服从上帝,这种服从,就是在个人领域内的绝对自由,因为不从属任何种类的人的控制和监督。另一方面,他对秩序和价值的需求以及征服本人和其他人身上邪恶力量的愿望,又使得他主张在政治领域中服从世俗权威”(《德意志人》,埃利希-卡勒尔著,商务印书馆)。出于这种考虑,路德创造性区分了精神自由和肉身自由,主张人应该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应该尽己所能在精神接近上帝的终极存在;同时,要求在世俗生活中,必须克制个人欲望和物质需求,通过服从和克己来摆脱生物本能力量对于自我的支配和控制,获致最大限度的精神自由。
在其他文化中,克己和苦行的观念虽然也时常被提及,但是通常难以成为主流和常态,或者需要借助类似于后世和因果报应这样的观念来帮助信仰者保持精神和情绪的平衡。例如,虽然中国理学中有“灭人欲,存天理”之说,但是中国的自由观中居主导地位的始终是“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式的天人合一,即精神-肉体相统一的自由观;而佛教的现世苦修思想与因果报应和轮回之间有着很难否认的心理关联。与此不同的是,德意志的自由观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洽的:通过区分精神自由和肉身自由,赋予精神自由某种终极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将精神上的自由和行动上的严谨守纪言之成理地统一起来。这种诠释的深层心理动因构成了德意志气质中独特和深刻的一面,也是“德意志力量”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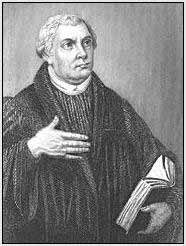 </P>
</P>
<P>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
<B>德意志气质:历史的光影</B>
写这一节时,恰逢7月20日。也许,58年前那段历史的几羽碎片,是这篇小文最好的总结。
Stauffenberg上校重伤之后,本可退役,就此离开战争和危险。可是责任感使他做出了相反的选择:“虽然我残废了,可是我还有一个神圣的使命要去完成。。。总参谋部的每一名军官都有责任行动起来,挽救德国”。他对病榻前的妻子如是说。7-20行动失败后,Stauffenberg未经审讯,即被忠于希特勒的军队枪决。
同样是出于责任感,Rommel沉思之后承诺:“我有责任做些事情来挽救德国。。。告诉他们,可以指望我”。说这番话时,Rommel已经达到了作为一个军人所能达到的荣誉颠峰,即使在敌人那里,他也受到了普遍的尊重。无论战争以何种方式结束,即使战败,也并不妨碍他继续自己体面的军人生涯和宁静的家庭生活。对Rommel个人来说,投身贝克的密谋集团是一场不公平的赌博,他几乎不可能再为自己赢得什么,却可能失去一切。但是,由某种可贵的品质所驱使,他做出一个最终为之牺牲生命的选择。
事实上,密谋者们在最后一次行动之前,并不缺乏必要的现实感,已不再对“体面的和平”抱任何幻想。他们清楚,自己的行为可能仅仅是一种象征、一个符号。但他们显然认为,人是值得为了正当的精神牺牲生命的:
“要不惜一切代价行动起来。即使不能成功,也必须尝试在柏林夺取权力。事情的关键已经不再是政变的实际目的,而是向世界和历史证明德国的抵抗者勇于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和这个目标相比,其他的事情已经不再重要。
“我们之中的人没有理由抱怨死亡,因为任何加入这个行列的人已经穿上了内萨斯的衬衫。只有当一个人愿意为信仰而牺牲时,他才得以建立自己的道义价值”。
以上言语出自Henning von Tresckow将军。长期在东线服役的Tresckow是密谋的主要发起人和策划者之一。不同寻常的是,严酷的生存之战并未使他成为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这种将实际事务中的精明干练和深沉的理想主义精神气质结合在一起的能力,是日耳曼民族的一个独特之处。事败后,Tresckow独自来到无人的阵地,用一颗手榴弹炸掉了自己的脑袋。
7-20事件的抵抗者们用自己的行动例示了德意志气质中最可贵和显著的特征:勇气、理想主义的精神力量和建立于清醒的现实感之上的自我牺牲。这些品质与由虚妄的宗教狂热所诱发的 “勇敢行为”有本质的区别。如同道德价值必须建立在人的自由意志和自主选择之上,勇气价值也必须建立在清醒的现实感之上。毕竟,在高楼屋檐上行走的孩子不是因为真正的勇敢,而是出于无知和虚妄。
在中国人眼里,密谋者最后的牺牲或许有些过于理想主义了。但是这种指责必然是出于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抵抗者在7-20事件中的牺牲精神和道德勇气始终在帮助战后的德意志民族重建自己的精神世界。这对德国人是尤为重要的,他们需要一种言之成理的形而上学和严肃的精神生活。
 </P>
</P>
<P>“如果不把生命看做是为神圣使命而必须履行的责任,一个人才可能怕死”
Claus Graf Stauffenberg(1907-1944)
</P>
在表面上看来,德意志气质中充满了矛盾。这些矛盾中的一些似乎是尖锐和根本性的。但是通过深入的考察不难获致这样一个结论:德意志气质所表现出的矛盾经常是源自观察者的误解和成见。事实上德意志气质不仅具有逻辑清晰的一致性,而且具有内在的稳定性。或许,正是后者使前者可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得以保持。
<P>德意志气质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理想主义的精神勇气(不幸,这是有争议的。但是作者希望这种出于误解的争议在随后的文字中将得以澄清)。今天的德意志气质所包含的主要精神内涵可以追溯到前基督教时代的古日尔曼神话。主神奥丁和他的勇士们在与魔界的战斗中同归于尽,世界也随之毁灭。这类悲剧性的结尾从希腊时代就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是日尔曼的悲剧更狂暴、刚健,具有一种可怕的冷静和客观。正义者没有获得任何安慰性的奖赏,即使仅仅是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奖赏。没有牺牲的光荣,也没有受难的神圣。甚至正义本身也随着她的承载者一起寂灭。客观而言,这个世界确实既无价值也无意义。“在日耳曼神话中,战争就是自然界的秩序,就是生命的基本要素”(《德意志人》,埃利希-卡勒尔著,商务印书馆)。
这种植根于久远历史中的刚健的集体无意识和发自天性的英雄主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成为德意志斯多葛主义世界观和精神气质的心理基础。并在尼采的哲学和瓦格纳的戏剧中获得了众所周知的诗意化的复兴和发扬。一位在一战中阵亡的普通德国士兵在他的家书中典型地总结了这一点:“德国人向来把死亡看做高尚人生的完成。。。”(《向死而生》,德国文化丛书,三联出版社)。这里,死亡不再是一种纯粹否定性的东西,而被赋予某种终极的积极意义。
如果说哲学和艺术由于具有一定程度的精英特征而可能缺乏最广泛的平民意义和统计一般性的话,那么通过考察作为一种大众化宣传手段的军歌可以有效弥补精英特征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为宣传必须面向大众,符合大众的心理状态和需要。以纳粹德国时期著名的《德国装甲兵之歌》和《德国伞兵之歌为例》:
德国装甲兵之歌
“。。。。。。
跃上那冲向胜利的通途!
如果我们为命运女神所抛弃,
如果我们从此不能回到故乡,
如果子弹结束了我们的生命,
如果我们在劫难逃,
那至少我们忠实的坦克,
会给我们一个金属的坟墓。”
(歌词译文)
“。。。。。
Und kehren wir nicht mehr,
Zur Heimat zurck,
Trifft uns die Todeskugel,
Ruft uns das Schicksal ab,
Ja Schicksal ab,
Dann ist unser Panzer
Ein ehernes Grab。”
(德文歌词)
 </P>
</P><P>德军战斗油画
德国伞兵之歌
“。。。。。。
同志们,那是有去无回的征途。
在遥远的东方有黑色的云彩,
来,不要失魂落魄,来!”
(歌词译文)
“。。。。。。
Kamerad, da gibt es kein zurueck。
Fern im Osten stehen dunkle Wolken,
Komm' mit und zage nicht, komm' mit!”
(德文歌词。歌词共三段,每一段均出现了“同志们,那是有去无回的征途。”)
 </P>
</P><P>德军战斗油画
在这两首以激励士气和纪律精神为目的军歌中,死亡(而并非失败,这个差别是意味深长的)被毫不隐讳地提及。这种不同寻常处理的源于建立在清醒的现实感之上的勇气,也源于对自我、死亡和责任的深刻而独特的理解所带来的精神力量,在一般意义上反映了古北欧神话所代表的独特死亡观念对于现代德意志民族的大众心理特征的深远影响。
纪律和服从是德意志民族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这里引人注目的原因不仅在于其自身的彰显性,还源自与德意志式勇气之间的“对立”。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兴亡》中表达了这样的诘责:“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在战场上视死如归。。。却在尘世的权威面前唯唯诺诺。。。”。类似的疑问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不同的思考者也就此给出过不同的答案。事实上,循着德意志斯多葛主义的精神源头,勇气和服从之间表面上的矛盾可以被自然和清晰地理解。
古日尔曼人始终被罗马文明所吸引着,即使最严酷的汪达尔日尔曼人也对罗马文明怀有深厚的敬意。但是本能中对自由的渴望和斯多葛气质却使得他们的灵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被罗马所代表的文明生活方式同化。战斗的天性使得日尔曼诸族成为罗马的保卫者,又不可避免地成为罗马的破坏者和征服者。罗马时期的保卫和破坏,服从和抗争,如同一个隐喻,暗示了德意志民族在其后颇为漫长的历史中的命运。
法兰克王国分裂后,由于天性中对自由的追求和或许过度的战斗精神,德意志人路易的领地上未能象西法兰克那样长时间地维持着一个基础稳固的统一民族国家。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来自日尔曼法兰克王室的秃头查理在高卢凯尔特人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权威,而这种权威的绝对性是大多数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德意志的土地上从未获得过的。神圣罗马帝国由于组织松散、内部的征战和罗马教廷势力的渗透而变得如此弱小,以致她经常无法象同时期的法国、西班牙甚至丹麦那样赢得大陆国家的尊敬。这使得德意志成为强大和弱小矛盾体。
幸运的是,曾经使得德意志人无法融入罗马文明的斯多葛气质最终将帮助德意志摆脱涣散和内部争斗的宿命。日尔曼诸部落毁灭罗马之后,某种不安和负疚感时时支配着作为胜利者的日尔曼诸王的情绪。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不安源于对秩序和圣化的价值体系的渴望,反映了德意志气质中一种深刻而独特的方面:强大的争取自由的倾向,与一种同样强大的为某种奉为神圣的秩序和权威而献身的冲动相互交织的精神需求。只有从斯多葛主义的视角中,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才可能真正得以消解:自我主义者的行为模式是一致而容易理解的,他们追求个人自由,在享受自由所带来的任何乐趣的时候也不会有患得患失的负疚感;但斯多葛主义忽视自我、追求使命和责任的本质诉求使得斯多葛主义者的个人幸福的的终极实现无法简单地通过自我需要的满足来达致,而必须借助于某种外在秩序和价值体系的认同。
 </P>
</P><P>条顿骑士
这种斯多葛气质在德意志漫长的历史中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逐渐得到了社会化或学院化的发展。如黑暗时代的亲兵制度、行会、条顿骑士团、晚近一些的普鲁士军官团,以及德意志古典理想主义。条顿骑士三誓言:“安贫,守贞,服从”和伊曼纽尔-康德的著名命题:“理应即能够”(Ought implies can,英译) 典型地反映了德意志斯多葛主义对于黑暗时代和古典时代德意志人的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影响。
使得德意志斯多葛主义在德语民族的精神世界中发生最广泛和深刻的作用,并根深蒂固地成为近、现代德意志人精神气质的基本要素的代表性事件或许应该归结为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和宗教改革领袖路德对德意志斯多葛主义的继承、发展和独特诠释。路德的宗教改革,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德意志民族完成了获致精神平衡与内心宁静的自我精神建构;另一方面,为德意志摆脱政治上的涣散和重新崛起奠定了心理-文化的基础,并争取了必要的政治环境。
路德首先是一个典型的德意志人。“在路德身上,抗争的冲动和服从的冲动同样强烈。。。一方面,他那叛逆的天性和对自由的渴望,使得他提倡在精神上只服从上帝,这种服从,就是在个人领域内的绝对自由,因为不从属任何种类的人的控制和监督。另一方面,他对秩序和价值的需求以及征服本人和其他人身上邪恶力量的愿望,又使得他主张在政治领域中服从世俗权威”(《德意志人》,埃利希-卡勒尔著,商务印书馆)。出于这种考虑,路德创造性区分了精神自由和肉身自由,主张人应该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应该尽己所能在精神接近上帝的终极存在;同时,要求在世俗生活中,必须克制个人欲望和物质需求,通过服从和克己来摆脱生物本能力量对于自我的支配和控制,获致最大限度的精神自由。
在其他文化中,克己和苦行的观念虽然也时常被提及,但是通常难以成为主流和常态,或者需要借助类似于后世和因果报应这样的观念来帮助信仰者保持精神和情绪的平衡。例如,虽然中国理学中有“灭人欲,存天理”之说,但是中国的自由观中居主导地位的始终是“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式的天人合一,即精神-肉体相统一的自由观;而佛教的现世苦修思想与因果报应和轮回之间有着很难否认的心理关联。与此不同的是,德意志的自由观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洽的:通过区分精神自由和肉身自由,赋予精神自由某种终极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将精神上的自由和行动上的严谨守纪言之成理地统一起来。这种诠释的深层心理动因构成了德意志气质中独特和深刻的一面,也是“德意志力量”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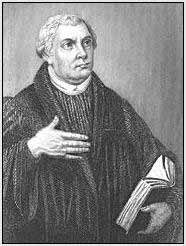 </P>
</P><P>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
<B>德意志气质:历史的光影</B>
写这一节时,恰逢7月20日。也许,58年前那段历史的几羽碎片,是这篇小文最好的总结。
Stauffenberg上校重伤之后,本可退役,就此离开战争和危险。可是责任感使他做出了相反的选择:“虽然我残废了,可是我还有一个神圣的使命要去完成。。。总参谋部的每一名军官都有责任行动起来,挽救德国”。他对病榻前的妻子如是说。7-20行动失败后,Stauffenberg未经审讯,即被忠于希特勒的军队枪决。
同样是出于责任感,Rommel沉思之后承诺:“我有责任做些事情来挽救德国。。。告诉他们,可以指望我”。说这番话时,Rommel已经达到了作为一个军人所能达到的荣誉颠峰,即使在敌人那里,他也受到了普遍的尊重。无论战争以何种方式结束,即使战败,也并不妨碍他继续自己体面的军人生涯和宁静的家庭生活。对Rommel个人来说,投身贝克的密谋集团是一场不公平的赌博,他几乎不可能再为自己赢得什么,却可能失去一切。但是,由某种可贵的品质所驱使,他做出一个最终为之牺牲生命的选择。
事实上,密谋者们在最后一次行动之前,并不缺乏必要的现实感,已不再对“体面的和平”抱任何幻想。他们清楚,自己的行为可能仅仅是一种象征、一个符号。但他们显然认为,人是值得为了正当的精神牺牲生命的:
“要不惜一切代价行动起来。即使不能成功,也必须尝试在柏林夺取权力。事情的关键已经不再是政变的实际目的,而是向世界和历史证明德国的抵抗者勇于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和这个目标相比,其他的事情已经不再重要。
“我们之中的人没有理由抱怨死亡,因为任何加入这个行列的人已经穿上了内萨斯的衬衫。只有当一个人愿意为信仰而牺牲时,他才得以建立自己的道义价值”。
以上言语出自Henning von Tresckow将军。长期在东线服役的Tresckow是密谋的主要发起人和策划者之一。不同寻常的是,严酷的生存之战并未使他成为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这种将实际事务中的精明干练和深沉的理想主义精神气质结合在一起的能力,是日耳曼民族的一个独特之处。事败后,Tresckow独自来到无人的阵地,用一颗手榴弹炸掉了自己的脑袋。
7-20事件的抵抗者们用自己的行动例示了德意志气质中最可贵和显著的特征:勇气、理想主义的精神力量和建立于清醒的现实感之上的自我牺牲。这些品质与由虚妄的宗教狂热所诱发的 “勇敢行为”有本质的区别。如同道德价值必须建立在人的自由意志和自主选择之上,勇气价值也必须建立在清醒的现实感之上。毕竟,在高楼屋檐上行走的孩子不是因为真正的勇敢,而是出于无知和虚妄。
在中国人眼里,密谋者最后的牺牲或许有些过于理想主义了。但是这种指责必然是出于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抵抗者在7-20事件中的牺牲精神和道德勇气始终在帮助战后的德意志民族重建自己的精神世界。这对德国人是尤为重要的,他们需要一种言之成理的形而上学和严肃的精神生活。
 </P>
</P><P>“如果不把生命看做是为神圣使命而必须履行的责任,一个人才可能怕死”
Claus Graf Stauffenberg(1907-1944)
</P><P>意志气质:决定论的进程
在表面上看来,德意志气质中充满了矛盾。这些矛盾中的一些似乎是尖锐和根本性的。但是通过深入的考察不难获致这样一个结论:德意志气质所表现出的矛盾经常是源自观察者的误解和成见。事实上德意志气质不仅具有逻辑清晰的一致性,而且具有内在的稳定性。或许,正是后者使前者可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得以保持。
<P>德意志气质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理想主义的精神勇气(不幸,这是有争议的。但是作者希望这种出于误解的争议在随后的文字中将得以澄清)。今天的德意志气质所包含的主要精神内涵可以追溯到前基督教时代的古日尔曼神话。主神奥丁和他的勇士们在与魔界的战斗中同归于尽,世界也随之毁灭。这类悲剧性的结尾从希腊时代就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是日尔曼的悲剧更狂暴、刚健,具有一种可怕的冷静和客观。正义者没有获得任何安慰性的奖赏,即使仅仅是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奖赏。没有牺牲的光荣,也没有受难的神圣。甚至正义本身也随着她的承载者一起寂灭。客观而言,这个世界确实既无价值也无意义。“在日耳曼神话中,战争就是自然界的秩序,就是生命的基本要素”(《德意志人》,埃利希-卡勒尔著,商务印书馆)。
这种植根于久远历史中的刚健的集体无意识和发自天性的英雄主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成为德意志斯多葛主义世界观和精神气质的心理基础。并在尼采的哲学和瓦格纳的戏剧中获得了众所周知的诗意化的复兴和发扬。一位在一战中阵亡的普通德国士兵在他的家书中典型地总结了这一点:“德国人向来把死亡看做高尚人生的完成。。。”(《向死而生》,德国文化丛书,三联出版社)。这里,死亡不再是一种纯粹否定性的东西,而被赋予某种终极的积极意义。
如果说哲学和艺术由于具有一定程度的精英特征而可能缺乏最广泛的平民意义和统计一般性的话,那么通过考察作为一种大众化宣传手段的军歌可以有效弥补精英特征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为宣传必须面向大众,符合大众的心理状态和需要。以纳粹德国时期著名的《德国装甲兵之歌》和《德国伞兵之歌为例》:
德国装甲兵之歌
“。。。。。。
跃上那冲向胜利的通途!
如果我们为命运女神所抛弃,
如果我们从此不能回到故乡,
如果子弹结束了我们的生命,
如果我们在劫难逃,
那至少我们忠实的坦克,
会给我们一个金属的坟墓。”
(歌词译文)
“。。。。。
Und kehren wir nicht mehr,
Zur Heimat zurck,
Trifft uns die Todeskugel,
Ruft uns das Schicksal ab,
Ja Schicksal ab,
Dann ist unser Panzer
Ein ehernes Grab。”
(德文歌词)
 </P>
</P><P>德军战斗油画
德国伞兵之歌
“。。。。。。
同志们,那是有去无回的征途。
在遥远的东方有黑色的云彩,
来,不要失魂落魄,来!”
(歌词译文)
“。。。。。。
Kamerad, da gibt es kein zurueck。
Fern im Osten stehen dunkle Wolken,
Komm' mit und zage nicht, komm' mit!”
(德文歌词。歌词共三段,每一段均出现了“同志们,那是有去无回的征途。”)
 </P>
</P><P>德军战斗油画
在这两首以激励士气和纪律精神为目的军歌中,死亡(而并非失败,这个差别是意味深长的)被毫不隐讳地提及。这种不同寻常处理的源于建立在清醒的现实感之上的勇气,也源于对自我、死亡和责任的深刻而独特的理解所带来的精神力量,在一般意义上反映了古北欧神话所代表的独特死亡观念对于现代德意志民族的大众心理特征的深远影响。
纪律和服从是德意志民族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这里引人注目的原因不仅在于其自身的彰显性,还源自与德意志式勇气之间的“对立”。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兴亡》中表达了这样的诘责:“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在战场上视死如归。。。却在尘世的权威面前唯唯诺诺。。。”。类似的疑问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不同的思考者也就此给出过不同的答案。事实上,循着德意志斯多葛主义的精神源头,勇气和服从之间表面上的矛盾可以被自然和清晰地理解。
古日尔曼人始终被罗马文明所吸引着,即使最严酷的汪达尔日尔曼人也对罗马文明怀有深厚的敬意。但是本能中对自由的渴望和斯多葛气质却使得他们的灵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被罗马所代表的文明生活方式同化。战斗的天性使得日尔曼诸族成为罗马的保卫者,又不可避免地成为罗马的破坏者和征服者。罗马时期的保卫和破坏,服从和抗争,如同一个隐喻,暗示了德意志民族在其后颇为漫长的历史中的命运。
法兰克王国分裂后,由于天性中对自由的追求和或许过度的战斗精神,德意志人路易的领地上未能象西法兰克那样长时间地维持着一个基础稳固的统一民族国家。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来自日尔曼法兰克王室的秃头查理在高卢凯尔特人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权威,而这种权威的绝对性是大多数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德意志的土地上从未获得过的。神圣罗马帝国由于组织松散、内部的征战和罗马教廷势力的渗透而变得如此弱小,以致她经常无法象同时期的法国、西班牙甚至丹麦那样赢得大陆国家的尊敬。这使得德意志成为强大和弱小矛盾体。
幸运的是,曾经使得德意志人无法融入罗马文明的斯多葛气质最终将帮助德意志摆脱涣散和内部争斗的宿命。日尔曼诸部落毁灭罗马之后,某种不安和负疚感时时支配着作为胜利者的日尔曼诸王的情绪。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不安源于对秩序和圣化的价值体系的渴望,反映了德意志气质中一种深刻而独特的方面:强大的争取自由的倾向,与一种同样强大的为某种奉为神圣的秩序和权威而献身的冲动相互交织的精神需求。只有从斯多葛主义的视角中,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才可能真正得以消解:自我主义者的行为模式是一致而容易理解的,他们追求个人自由,在享受自由所带来的任何乐趣的时候也不会有患得患失的负疚感;但斯多葛主义忽视自我、追求使命和责任的本质诉求使得斯多葛主义者的个人幸福的的终极实现无法简单地通过自我需要的满足来达致,而必须借助于某种外在秩序和价值体系的认同。
 </P>
</P><P>条顿骑士
这种斯多葛气质在德意志漫长的历史中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逐渐得到了社会化或学院化的发展。如黑暗时代的亲兵制度、行会、条顿骑士团、晚近一些的普鲁士军官团,以及德意志古典理想主义。条顿骑士三誓言:“安贫,守贞,服从”和伊曼纽尔-康德的著名命题:“理应即能够”(Ought implies can,英译) 典型地反映了德意志斯多葛主义对于黑暗时代和古典时代德意志人的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影响。
使得德意志斯多葛主义在德语民族的精神世界中发生最广泛和深刻的作用,并根深蒂固地成为近、现代德意志人精神气质的基本要素的代表性事件或许应该归结为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和宗教改革领袖路德对德意志斯多葛主义的继承、发展和独特诠释。路德的宗教改革,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德意志民族完成了获致精神平衡与内心宁静的自我精神建构;另一方面,为德意志摆脱政治上的涣散和重新崛起奠定了心理-文化的基础,并争取了必要的政治环境。
路德首先是一个典型的德意志人。“在路德身上,抗争的冲动和服从的冲动同样强烈。。。一方面,他那叛逆的天性和对自由的渴望,使得他提倡在精神上只服从上帝,这种服从,就是在个人领域内的绝对自由,因为不从属任何种类的人的控制和监督。另一方面,他对秩序和价值的需求以及征服本人和其他人身上邪恶力量的愿望,又使得他主张在政治领域中服从世俗权威”(《德意志人》,埃利希-卡勒尔著,商务印书馆)。出于这种考虑,路德创造性区分了精神自由和肉身自由,主张人应该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应该尽己所能在精神接近上帝的终极存在;同时,要求在世俗生活中,必须克制个人欲望和物质需求,通过服从和克己来摆脱生物本能力量对于自我的支配和控制,获致最大限度的精神自由。
在其他文化中,克己和苦行的观念虽然也时常被提及,但是通常难以成为主流和常态,或者需要借助类似于后世和因果报应这样的观念来帮助信仰者保持精神和情绪的平衡。例如,虽然中国理学中有“灭人欲,存天理”之说,但是中国的自由观中居主导地位的始终是“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式的天人合一,即精神-肉体相统一的自由观;而佛教的现世苦修思想与因果报应和轮回之间有着很难否认的心理关联。与此不同的是,德意志的自由观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洽的:通过区分精神自由和肉身自由,赋予精神自由某种终极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将精神上的自由和行动上的严谨守纪言之成理地统一起来。这种诠释的深层心理动因构成了德意志气质中独特和深刻的一面,也是“德意志力量”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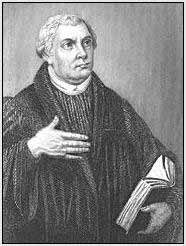 </P>
</P><P>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
<B>德意志气质:历史的光影</B>
写这一节时,恰逢7月20日。也许,58年前那段历史的几羽碎片,是这篇小文最好的总结。
Stauffenberg上校重伤之后,本可退役,就此离开战争和危险。可是责任感使他做出了相反的选择:“虽然我残废了,可是我还有一个神圣的使命要去完成。。。总参谋部的每一名军官都有责任行动起来,挽救德国”。他对病榻前的妻子如是说。7-20行动失败后,Stauffenberg未经审讯,即被忠于希特勒的军队枪决。
同样是出于责任感,Rommel沉思之后承诺:“我有责任做些事情来挽救德国。。。告诉他们,可以指望我”。说这番话时,Rommel已经达到了作为一个军人所能达到的荣誉颠峰,即使在敌人那里,他也受到了普遍的尊重。无论战争以何种方式结束,即使战败,也并不妨碍他继续自己体面的军人生涯和宁静的家庭生活。对Rommel个人来说,投身贝克的密谋集团是一场不公平的赌博,他几乎不可能再为自己赢得什么,却可能失去一切。但是,由某种可贵的品质所驱使,他做出一个最终为之牺牲生命的选择。
事实上,密谋者们在最后一次行动之前,并不缺乏必要的现实感,已不再对“体面的和平”抱任何幻想。他们清楚,自己的行为可能仅仅是一种象征、一个符号。但他们显然认为,人是值得为了正当的精神牺牲生命的:
“要不惜一切代价行动起来。即使不能成功,也必须尝试在柏林夺取权力。事情的关键已经不再是政变的实际目的,而是向世界和历史证明德国的抵抗者勇于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和这个目标相比,其他的事情已经不再重要。
“我们之中的人没有理由抱怨死亡,因为任何加入这个行列的人已经穿上了内萨斯的衬衫。只有当一个人愿意为信仰而牺牲时,他才得以建立自己的道义价值”。
以上言语出自Henning von Tresckow将军。长期在东线服役的Tresckow是密谋的主要发起人和策划者之一。不同寻常的是,严酷的生存之战并未使他成为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这种将实际事务中的精明干练和深沉的理想主义精神气质结合在一起的能力,是日耳曼民族的一个独特之处。事败后,Tresckow独自来到无人的阵地,用一颗手榴弹炸掉了自己的脑袋。
7-20事件的抵抗者们用自己的行动例示了德意志气质中最可贵和显著的特征:勇气、理想主义的精神力量和建立于清醒的现实感之上的自我牺牲。这些品质与由虚妄的宗教狂热所诱发的 “勇敢行为”有本质的区别。如同道德价值必须建立在人的自由意志和自主选择之上,勇气价值也必须建立在清醒的现实感之上。毕竟,在高楼屋檐上行走的孩子不是因为真正的勇敢,而是出于无知和虚妄。
在中国人眼里,密谋者最后的牺牲或许有些过于理想主义了。但是这种指责必然是出于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抵抗者在7-20事件中的牺牲精神和道德勇气始终在帮助战后的德意志民族重建自己的精神世界。这对德国人是尤为重要的,他们需要一种言之成理的形而上学和严肃的精神生活。
 </P>
</P><P>“如果不把生命看做是为神圣使命而必须履行的责任,一个人才可能怕死”
Claus Graf Stauffenberg(1907-1944)
</P>
德国—日尔曼,复杂的情感